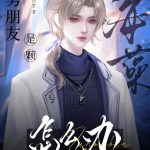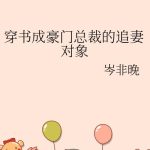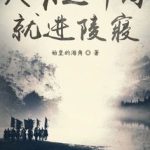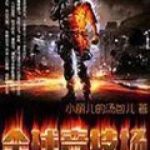瑤花微笑:“是嗎?有誰見到将朱大人丢下水的人是我了?”
鳳凰別過頭去一言不發,伏日升照例只有苦笑。
錢汝珍也只好苦笑。
【十二、】
三個月後,當姬瑤花一行人終于取藥回來,小魚卻已經悄然離去。
留給姬瑤花一封只有三個字的信:謝謝你。
還有那枝分水蛾眉刺。
伏日升狐疑不定地打量着這枝蛾眉刺:“小魚這是什麽意思?”
姬瑤花輕嘆一聲:“小魚不等藥服完便離開,只怕這輩子都不能複原、不能再成為峽江之上的龍女了。這枝蛾眉刺是向集仙峰護法長老求取武功心法的信物。小魚交給我,也就是要我替她尋找下一個傳人。我想她雖然不算喜歡我,畢竟還是佩服我的吧。”
伏日升皺皺眉:“我怎麽覺得你的解釋非常牽強呢?”
他的心裏很不舒服。他枉自為小魚奔忙了那麽長的時間,到頭來小魚還是選擇站到了幾乎害死她的姬瑤花一邊。
姬瑤花的笑意裏含着淡淡的無奈:“伏師兄,你終究不能真正了解小魚。而我,我已觀察她兩年。也許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”
無論她如何想盡辦法将小魚推到朱逢春身邊,小魚終究還是選擇離開。
只因小魚深知,朱逢春是她不能接近、無法擁有的那類人。
而這三個月,将是小魚一生的甜蜜回憶。
足以彌補她漫長的守候與等待。
所以她才會給姬瑤花留下那三個字,留下姬瑤花想從她身上得到的東西。
姬瑤花出了一會神,又嘆息了一聲:“懸崖撒手。唉,我自以為已經很了解小魚了,卻還是沒有想到她會有這樣的大勇氣大智慧。”
說到此處她眼波流轉,瞟了朱逢春一眼,微笑道:“小魚若是留下來,朱大人必定會覺得很為難;但是小魚這一走,只怕朱大人一輩子都忘不了她了。”
她的話鋒直刺人心,朱逢春饒是見慣風雲,也感到難以招架,只有望向伏日升,兩人相對苦笑。
許多年以後,當朱逢春坐在臨安樞密院的公案後,埋首于堆積如山的公文時,總會在出神時不自覺地想到當年那個奇異的姑娘。
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将她留在身邊,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将她留在身邊。
但是小魚的身影伴随了他一生。
【後記:巫山十二峰之集仙峰】
集仙峰為巫峽北岸自東而西第一峰,傳說古時每逢中秋之夜,就有一群仙女來峰頂聚會,因而名之為“集仙峰”。峰上有各種形态的巨石林立,峰頂則岔成兩座小峰,酷似一把張開的大剪刀,故此又名剪刀峰。
如剪刀一般的峰頂,也可以看作是張開的魚尾,因此設定集仙峰弟子精于水戰,宛若魚龍。
之四:地獄變
【一、】
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雲:大荒之中有靈山,共有十六巫出沒此地,溝通天地。神農氏之時,“右手操青蛇,左手操赤蛇”的巫鹹,于諸巫之中被選拔出來主持天下巫筮之事,由此地位超然于衆巫之上。黃帝與炎帝争涿鹿之野,将戰之際,也曾蔔筮于巫鹹。唐堯之時,巫鹹生前封于此山,死後葬于此山,故此山改而以巫為名,世人也稱為巫鹹山。山下人煙聚湊,漸成都邑,漢時設縣,稱巫縣,隋時始用巫山縣之名。
巫山縣治,依山而起,大街小巷共有十二條,分別以巫山十二峰命名。城臨大寧河寬谷與巫峽臨界處,城邊江面開闊,大水時寬達近兩裏;下游甚近處即入峽谷,江面寬度驟然減至不足半裏,水流異常湍急。此地一年四季,水位變化多端,船碼頭處,一列水尺由江灘直上山坡,每年桃花汛之際,在此看水,極為壯觀。
巫山縣治內,古意盎然,不但上古之巫風猶存,如歐陽修公所詠:游女髻鬟風俗古,野巫歌舞歲時豐;數千年來,更有無數神跡流傳不息,鄉民世世奉祀,不敢怠慢,其中最為鄉民所重的祭祀莫過于藥王廟與巫女祠。
藥王廟在縣城之西松巒街的盡頭,一說是祭神農。相傳神農氏遍嘗百草,救治天下病患,在巫山一帶,停留時間最長,至今巴東縣治之東仍有溪以神農命名,故鄉民立廟紀念。另一說是祭巫鹹。上古之時,巫醫不分,神巫也是神醫。鄉民無知,籠統而言,一概稱為藥王,立廟祭祀,歲時供奉,遇有大病,更是虔誠叩拜,焚香許願。說也奇怪,鄉民許願之後,往往有不藥而愈者,這等神跡,口耳相傳,以至于巴蜀湘楚之民,若有重病,當地郎中難醫,往往不遠千裏前來叩拜,據傳求者若心誠志堅、命不該絕,自有神人搭救,便是沉苛,也能起死回生。
巫女祠在縣城之東起雲街的盡頭,所祭之神,鄉民稱為巫山之女或曰巫山小女。至于這巫女究竟是何人,鄉民同樣含混不清。巫女祠的前身,原是楚國祀高媒之地,看起來這巫女似是主掌世人婚姻的神也即女娲;但此後楚民祭祀出沒無常的諸多女神如梅山娘娘、花林娘娘,往往也都在此地,巫女祠由此竟成了巴蜀湘楚之民祭祀各方女神的聖地。求子女、求婚姻乃至于各種對佛道正神不能開口的隐秘心事,盡可以向代掌神職的巫女祈求,若有緣分,巫女自會轉告女神,滿足求者心願。
巫山縣因為有了這香火繁盛的兩大祠廟,雖然僻處深山,仍是人煙輻湊,當地特産之藥材、烏桕、生漆、梨子等由此得以流販各地,當地居民,往往只須坐收客棧與貨棧的租金,便可得到豐裕的收入,是以家給人足,悠閑自在。
論理,巫山縣每年歲入豐厚,百姓富足,巫山縣令應是頭等好差。
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。
歷任巫山縣令,最頭痛的經,便是為巫山縣帶來滾滾財源的藥王廟與巫女祠。
常言道,一山不容二虎。
這句話的真假沒有人求證過,但是看起來一城不容二神倒是千真萬确的。
巫山縣沒有天下縣城都應有的城隍廟,想來城隍在此處也安身不下。
藥王與巫女,沒有一個是好惹的啊。
主持藥王廟日常事務的廟祝,當地鄉民稱為端公,若有祈求,先訴端公,端公轉訴給人間藥王——巫山門十二弟子中的松巒峰弟子,自會有所回答。
主持巫女祠日常事務的道姑,當地鄉民稱為師婆,若有祈求,先訴師婆,師婆轉訴給人間巫女——巫山門十二弟子中的起雲峰弟子,方能回應。
刻薄人私下裏稱為“巫山十二瘋”的巫山十二弟子,往往性情古怪,行事随心所欲,本就是些禍端。
再加上對他們視若神明的愚昧鄉民……
巫山縣令的頭還真不是一般地痛。
每年春節,四方鄉民前來祭祀之際,也是巫山縣令如臨大敵、頭痛欲裂之時。
熱鬧非凡的祭祀,不知何時,轉眼間便會演變成兩派人馬的群毆,甚至于派出去彈壓的衙役,也會因為立場不同而忘乎所以地參與群毆。
神宗年間的一次祭祀,死傷太多,事情鬧得也忒大了,一位宮廷畫師适逢其會,将當時慘狀繪成一幅《巫山血祭圖》,上呈官家,朝堂為之震動;其時王安石當政,考察官員又甚是嚴格,巫山縣令恐懼之下,請示朝廷暫停一年祭祀。但是祭祀之風,綿延數千年,豈是一紙诏令能夠禁得住的?難免民怨沸騰。加之四方來客絕跡,稅收劇減,于是第三年便不得不開禁。
一禁一放,威嚴盡失,鄉民越發視朝廷诏令為無物,此後便是想禁也禁不住了。
至徽宗年間,這群毆之風,竟是越演越烈。
時任巫山縣令的,原是閩中名士,枉有文名,對此亂象,卻無法可想,只有挂冠求去,寧可降職也要調往他處。
其時一年一度的歲末祭祀就将到來,朝廷诏令下來,着任巴東縣令尚未期滿的朱逢春,轉調巫山縣令,不須再入京敘職;原巴東縣令的職守,也暫時由他署理,直到新縣令到職為止。
一人兼署兩縣,雖是暫時的,這在大宋,也算是驚世駭俗的特例了,足見朝廷對朱逢春的倚重與賞識。
原任巫山縣令如釋重負,一交了印,便匆忙離去。
将這個難題留給了素有幹練之名的朱逢春。
若是能解開這道難題,朱逢春不過博得一句“名不虛傳”的稱贊,一個原本已成定數的“卓異”的考語;若是不能,只怕此前的努力都要付諸東流了。
歷來都道是能者多勞,朱大人這一回,臨危受命,也算是受盛名之累了。
【二、】
松巒街盡頭的藥王廟前,瘦小得像只猿猴的老端公雙手籠在袖中,拿一個薄團坐在